蓝江 |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当我们出现在一个荒岛上,周围只有很简单的材料,我们怎样用这样的材料为自己修建一个可以栖身的居所?我们如何掌握好新的技术,来抵御各种动物和僵尸、骷髅的进攻?我们如何依靠采集果实、种植作物、捕猎甚至烹饪来维持一个虚拟界面上的生命?对于这些命题,那些曾经玩过《我的世界》或《明日之后》的玩家十分熟悉,他们不仅可以回答这些问题,而且可以轻车熟路地在那个由数字代码组成的世界,每日每夜用自己的行为来实践这些活动。 换言之,这些游戏及其活动已经成为21世纪新生代人的日常生活,不仅是那些天天刷着《王者荣耀》《明日之后》《荒野行动》的玩家在用游戏的方式建构着自己的日常经验,就是那些在地铁和闲暇时刷着《开心消消乐》《斗地主》《跳一跳》的白领,也在用游戏的方式来阐释自己的生活。是的,这是游戏的一代,正如20世纪50、60年代的人往往用阅读书本的方式来理解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而70、80年代的人用电视的方式来理解金庸先生笔下令狐冲的放荡不羁、郭靖的侠之大者以及韦小宝的古怪精灵;而今天的90后以及21世纪的新世代早就在用电脑游戏或其他游戏的方式直接参与到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之中。习惯于阅读小说和看电视的一代人,很难理解当IG战队在2018年斩获了英雄联盟S级系列赛事总决赛的冠军时,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悦。所以,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不应简单地将游戏这个现象视为洪水猛兽,将之当作荼毒青少年的电子鸦片,而是需要理解游戏本身与今天的年轻一代之间的生存关系。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哲学或存在论上的反思,从游戏式生存的内部来寻找其独特的运行逻辑。 在思想史上,对于游戏问题的思考,最深入的思想家无疑是荷兰人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他的名著《游戏的人》(Homo Ludens)中,游戏是一个单独的世界,从而让自身与日常生活的节奏分离开来:“我们发现游戏处处表现出一种明显确定的行动品质,从而有别于‘平常’生活……在素有的活动中,这一品质判然有别,它赋予我们称之为‘游戏’的生活形式以特有的东西。” 游戏,在赫伊津哈那里,对于人类来说,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活动,赫伊津哈将人类的活动分为三种:一是思考的人(homo sapiens),这样的人是一种理性和思维的存在物。而生产的人(homo faber)从事着日复一日的生产性活动,并不断地再生产出人类的文明世界。不过,对于赫伊津哈来说,所有人类的伟大创造,都是游戏的人活动的结果,游戏产生了人类的文化,并将之升华为人类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当人类与其他自然世界的事物相区别的时候,意味着人类在游戏状况下实现了对世界的超越和构建。这样,我们可以按照赫伊津哈的逻辑得出结论,人类世界的文明,乃至一切意义,都与从事游戏形式的人的活动有关,这意味着,文明或意义是游戏的人的创造,所有的意义归根结底应该还原为游戏的活动。正如赫伊津哈所说:“我们必须归结起来,文明在其最初阶段是一场游戏。但是它并不能像婴儿脱离母胎一样从游戏中分离,它在游戏中升起,并永远不离开游戏的母胎。” 不过,赫伊津哈的游戏问题是一个泛化的游戏概念,当我们用这个概念来思考今天的电子游戏的时候,尽管仍然具有相似的地方,如电子游戏仍然保持为一个独立于日常生活的世界,但是,这种游戏的行为是否仍然具有赫伊津哈赋予游戏的审美和精神上的意义?当代游戏文化研究学者米格尔·斯卡特(Miguel Sicart)评价道:“赫伊津哈的观念,对于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只能算是一般,不过,他的思想仍然能够启迪我们如何去理解游戏,尽管他的《游戏的人》一书已经相当过时了。”的确,今天的电子游戏,不能用席勒式的崇高来理解,也无法上升到了赫伊津哈的精神创造的维度。今天的电子游戏,是一种普通的日常生活,是我们在闲暇时,甚至忙里偷闲时打开电脑上的应用程序或手机上的APP的活动。所以,从精神创造的层面来拔高游戏的地位,或者如赫伊津哈将游戏的人放在先于思考的人和生产的人之前的优先地位,显然是不恰当的。 法国思想家梅洛-庞蒂是另一个思考游戏问题的重要渊源。梅洛-庞蒂并不像赫伊津哈一样希望在一种游戏的精神升华中来理解游戏与我们周遭的文明世界的意义。他认为我们并不是依赖于某种先天观念来实现了在世界上存在,恰恰相反,我们的身体构造出我们在世界上的意义和空间构成。 在《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中,梅洛-庞蒂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身体对我们在世界上的空间和意义的建构性作用:我们的生存与世界的联系的关键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身体行为在世界上找到让我们可以栖居的空间,从人类起源开始,人用身体制造了衣服和最简单的工具,这些工具构成了所谓的文化世界。所以,所谓的文化,并不是一开始就与赫伊津哈的那种抽象的游戏活动有关,游戏活动最根本的界面是身体。古时候的游戏,无论是相扑,还是投壶,甚至蹴鞠和马球,最根本的是一种身体的活动,这样,在身体的延伸和对自然空间的抵抗和克服中,创造了属于身体,也同时属于人的存在的空间和意义。这个世界是一种身体性的筑造,身体是我们在游戏中存在的最根本的点。 梅洛-庞蒂将身体范畴上升到存在论的高度,他指出:“存在着作为一堆相互作用的化学化合物的身体,存在着作为有神明之物和它的生物环境的辩证的身体,存在着作为社会主体与他的群体的辩证的身体,并且,甚至我们的全部习惯对于每一瞬间的自我来说都是一种摸不着的身体。”这意味着,世界是相对于我们的身体而展开的,或者反过来说,我们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来触及世界的,世界即我们身体所介入的世界,世界的意义也在我们的身体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生成一个意义和空间的世界。这样,身体不仅仅是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方式,也是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的现象学——身体现象学。我们的身体及其行为,为我们揭示了世界的意义,同时,世界也向我们展现为属于我们身体的世界,这是一种辩证的身体,身体既在做着有机生命的循环运动,也在向我们展现属于文化和精神层面的东西。在电子游戏之前,身体成为我们参与游戏最终的支撑点,也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之锚。 的确,在电子游戏之前,除了身体之外,我们的确再也找不到另一个支点,让我们的行为支撑起在世存在的结构。即便是阅读小说、观赏艺术作品、看电视和电影,实际上都没有摆脱这种身体性的构成。例如,梅洛-庞蒂断定:“电影不向我们提供人的思想,它给我们提供那个人的举止或行为,把在世存在,待人接物的那种特殊的身体方式直接提供给我们,那种方式对我们而言,显见于身体姿态、目光、手势表情,它显而易见地界定着我们所认识的每一个人。”也就是说,尽管文学、艺术和电影也创造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相对于日常生活的世界也保持了一定独立性,但是,我们对这样的世界的把握依然是从当下我们的身体来把握的。例如在看《侏罗纪公园》的时候,霸王龙突然出场,不仅吓坏了电影中的角色,随着斯皮尔伯格的灯光、声音和镜头特写,处在屏幕前的我们的身体也切身地体会到面对霸王龙的恐惧,我们的身体也参与到电影影像的构建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电影的感触(affect)依然是身体性的,同时,依照这种感触建构起来的电影的意义也是在身体的行为下生成的。 不过,在电子游戏时代,这个问题或许会发生一点变化。比如,在早期的任天堂游戏机上的《超级马里奥》(Super Mario Bros.)上,能够从电视屏幕从左向右移动的游戏角色,能够踩死怪物,也可以从宝箱里顶出一个蘑菇变大,变得更有力量。在表面上,这个角色接受着我们使用游戏手柄的操纵,但是,对于曾经玩过类似任天堂游戏的玩家来说,操纵这个角色不像我们看电影那样单纯,这个角色总是在以某种方式抵抗着我们的操纵。例如,你在快速指挥马里奥奔跑跳跃一个十分宽阔的壕沟的时候,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结果掉入壕沟之中。在你信心十足地躲过一个按规律运动的火把时,马里奥的身子正好被火把剩余的火苗烧到,游戏结束。正如格雷格·科斯蒂克杨(Greg Costikyan)所说:“总而言之,在《超级马里奥》中,你们的表现充满了不确定性——你是否能熟练掌握游戏中的手眼协调能力,来战胜各种难关。你们或许最终在‘通关’游戏之前会失败很多次。你们不稳定的技能展现出的不确定性,以及你们没有确定的能力时时刻刻集中精力玩游戏,这就是游戏产生吸引力的核心。” 这里问题并不是说,在电子游戏中的世界意义的构建不再依赖于身体,恰恰相反,梅洛-庞蒂的身体经验和身体现象学在这里仍然是起作用的。但是,与阅读小说和看电影的经验不同,这里不止一个身体在建构着意义,一个电子游戏中作为代码和算法的身体,时时刻刻在抵抗着我们身体的操纵。身体从单数的大写身体,突然分裂了,我们在电子游戏中感受到另一个身体的存在,那个马里奥,作为一种独特性的身体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着我们曾经被视为唯一的身体存在。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游戏不是唯一的,我们往往在不同的游戏世界里穿梭,而在每一个世界里的身体都有着不同的属性,不同的行为,也建构着不同的空间和意义。例如育碧出版的《刺客信条》(Assassin Creed)系列,角色的行为面对的是一个尚未敞开的地图,而游戏玩家的每一次探索,所打开的世界是不同的,每一次构筑的身体经验也不同,在最新的版本中,游戏玩家可以骑马驰骋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之中,可以在雅典、斯巴达、科林斯、温泉关来回穿梭,也可以驾驶着三桅帆船游弋在地中海之中。我们的经验在这样的世界中被拓展、被架构,我们不再是在临近世界里理解我和周遭世界的关系的身体,而是一个可以在游戏经验里被拓展和延伸的身体经验。这种身体经验,毋宁是一种数字式的算法经验,这种代码算法在一个彼此独立的数字算法空间重构着身体,也重构着意义。于是,我们的身体分裂了,那个被梅洛-庞蒂作为存在之锚的身体被分裂为多个身体,成为我们在游戏世界中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多元性存在。 或许,我们可以说,这已经不是梅洛-庞蒂或米歇尔·亨利意义上的身体现象学,而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学。由于游戏世界中的身体是由数码和算法构成的,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新的名称——数码现象学。当然,在电子游戏充斥着互联网的今天,说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已经过时了,的确为时尚早,但是,我们的确面对着一种不同的现象学——数码现象学,而数码现象学在游戏世界里构筑起来的新的经验,必然会挑战那个唯一身体的现象学和存在论的权威性。正如在电影《头号玩家》中,给人留下深刻记忆的究竟是那个在现实世界中的韦德,还是他在绿洲世界中的数码身份或虚体(virtual body):帕西法尔?当帕西法尔在赛车游戏中拿到绿洲的第一把钥匙时,在排行榜上出现的是他的数码身份——帕西法尔,韦德是隐匿的,不为人所知,一个数码世界的英雄和现实中租住在贫民窟里的无业青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需要我们走得更深一些,看看在这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德勒兹的《两种疯狂体制》(Deux régimes de fous)的开头,他谈到了克莱斯特(Kleist)笔下的提线木偶傀儡师,与其他的木偶不同,提线木偶的操纵并不是按照真正的人体运动的方式来实现的,“傀儡师并不是按照人物将要呈现的动作来操纵木偶。他是用一根垂线来操纵他的木偶的,或者说他替换了木偶的重心,更准确地说,他让木偶变得轻巧。” 实际上,整个木偶与傀儡师之间的关系是由三种不同的线条构成的。 第一条是最显著的表象的线,即木偶向我们呈现出来的运动,木偶在傀儡师的操纵下,做出与真人相差无几的动作,如走路、坐立、跳跃甚至彼此间的对战,这条线索向我们展现出来的是木偶剧叙事需要向我们说明的故事,所以人物的安排和行动,都依从这个线索。一个熟练的傀儡师,可以惟妙惟肖地展现出一个木偶的灵活运动,在傀儡师的技艺下,这个木偶仿佛具有了活的灵魂,似乎与那个在幕后的人没有关系,他们似乎在自己演出着整个故事。 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无论台前的提线木偶多么灵活,模仿得多么像人,最重要的控制权在幕后的那个傀儡师手上,但是傀儡师与木偶之间不是直接联系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真实的,但并不需要被台前的观众看到的线,这些线构成了傀儡师掌控木偶的直接手段。有趣的是,在这个运动中,最真实的线恰恰是不需要被看到的,如同武侠电影中的吊威亚一般。我们虽然都知道演员在空中的飞翔是由实际的钢丝形成的,但是这个钢丝是观众会有意或者无意地选择忽略的,也唯有忽略了演员背后的钢丝,我们才能看到电影中神乎其技的武侠的存在。同样,在提线木偶中,提线是实然的存在,也是观众在观看木偶剧时选择忽略的东西,即便那根线在台前若隐若现,但观看木偶剧的观众似乎都看不到它的存在。 这样,一个有趣的辩证关系在提线木偶剧中出现了:一个虚假的运动,即木偶的运动被观众当成真实的运动;而一个真实的运动,即提线运动,被观众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个辩证关系是让提线木偶剧得以成立的前提,如果我们需要连贯地欣赏一部木偶剧,这种颠倒的辩证法是需要的。因为,若我们不想做一个专业的提线木偶的傀儡师,我们就不需要了解真实提线的运动,那个虚假的运动支撑着整个叙事和意义的展开。 除了上述两种线条之外,德勒兹还提出了第三种线条。按照德勒兹的说法,这是一根真正的无形之线。相对于提线运动,这根线根本没有物理上的存在,但是它却支配着整个提线木偶剧的规则和架构,换句话说,这是让提线木偶剧成为提线木偶剧的东西,这个架构体系不是直接敞开的,无论对于台前的观众,还是对于幕后的傀儡师,这根线都没有直接呈现出来,它只有在木偶剧的演出构成中,以某种失误或不确定的方式显现出来,它将木偶剧的行为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依照一个隐形的线索支配着木偶剧的运动。 如果我们将这三条线索套用在游戏上会如何呢?以早期的任天堂游戏《超级马里奥》为例,在电视画面上显现出来的是那个穿着工装裤的水管工的运动,他不停地在卷轴式画面上顶宝箱、踩乌龟、钻水管、跃壕沟,在每一关卡的背后跳过一个高台,最终降下城堡的旗帜,登上城堡。在游戏过程中,无论怎么操作,马里奥的动作都是连贯的。但是,对于电视面前的玩家来说,却不是如此。马里奥的运动是他们通过游戏机的手柄来实现的,他们的活动与向右运动的前进键,与按照B键构成的加速键,以及A键跳跃键有关,这些通过电线连接传导的运动,实际上是真实的运动,类似于提线木偶中的提线运动,玩家掌控着画面中的游戏角色的运动。 在一些更复杂的早期游戏中,如《街头霸王》《侍魂》《拳皇》等对战类游戏,如操纵穿着白色战衣的Ryu,玩家可以在操纵杆上划出↓↘→加上攻击键就能使出远程攻击的波动拳,→↓↘加上攻击键就是升龙拳,这些动作在街机屏幕上显现为一系列的制敌招数,对于有着长期经验的街机玩家来说,这些特殊的招数,只有在经过反复练习之后,才能在对战时使用。游戏画面中流畅而华丽的攻击,与操纵者熟练应用操纵杆和手柄密切相关。在今天更为复杂的手机游戏和电脑游戏中,这种特殊的控制技艺的设定并没有过时,如在《刺客信条》中,玩家可以通过键盘对人物进行操纵,在悬崖峭壁上攀爬,靠近敌人之后,可以用刺杀键悄无声息地将敌人刺杀。这些就是第二根线,即玩家相对于游戏角色的提线运动。 那么,什么是第三根线?第三根线与游戏设定的框架有关,比如说,我们为什么玩游戏?我们究竟从游戏的娱乐中获得了什么?在一般的游戏设定中,游戏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倒最终的大Boss,但是,大Boss的死去是否意味着游戏的结束,如在《无尽之剑3》中,两位主角可以成功地杀死被称为锁匠的Boss,游戏的叙事情节也在此结束,但是,游戏还有其他的设定,如女主角在一个之前不起眼的地方战胜一个比Boss更厉害的角色莱斯后会获得最强装备太阳剑,而寻找这把太阳剑,战胜莱斯成为了游戏玩家更大的乐趣。还有诸如《神庙逃亡》这种根本没有结束的终点的游戏,实际上如何获得更多的宝石装备或者更高的分数成为支撑玩家继续下去的动力。 这里或许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反转,可以借用科耶夫版的主奴辩证法来进行思考。在黑格尔那里,主奴辩证法被用来作为证明自我意识的一个例证,主人作为自为存在,“通过独立存在间接地使自身与奴隶相关联,因为正是这种关联,奴隶才成为奴隶”。黑格尔的原意是说,主人是通过奴隶的中介与物或对象发生关系,最终达到欲望的满足,而奴隶代替主人行使了面对对象的能力,实现了主体的自为存在。不过,在科耶夫那里,这种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换。科耶夫说:“主人之所以是主人,仅仅在于他的欲望不针对一个物体,而是针对另一个欲望,因为有一种被承认的欲望。另一方面,在成为主人后,作为主人,他必须寻求得到承认,只有他把另一个人当作奴隶,他才能被承认是主人……因此,主人走错了路。在使之成为主人的斗争之后,他并没有成为在进行这种斗争时他所希望成为的人,被另一个人承认的一个人。所以,如果人只能通过承认才能得到满足,那么主人身份行事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 我们可以简要地分析一下科耶夫的论证:(1)最初的主人和奴隶的构成是主人通过奴隶指向物的,主人对对象或物欲望的满足必须通过奴隶的中介,在这个时候,主人的欲望是物,是对象,奴隶只是满足这个欲望的中介。(2)奴隶成为中介的前提条件是奴隶必须承认主人为主人,也就是说,一旦奴隶不承认主人为主人,主人的欲望就无法满足,从而主人存在着不被承认的危险。(3)主人的欲望发生了改变,即他的欲望不再指向对象或物,而是指向奴隶的承认,为了得到奴隶的承认,主人必须成为奴隶的欲望,即奴隶欲望承认主人,这就是对欲望的欲望。简言之,主人需要成为奴隶(或他者)的欲望,才能成为对欲望的欲望。 巴迪欧曾有一个很精彩的评价:“对他者欲望的欲望,去获得他者欲望的欲望。这样,我们在这里看到,在主体本身最核心的地方,主体的构成依赖于他者,这种依赖不仅仅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主体的身份对他者的依赖,不仅仅是从其来源,或可能性,或社会关系等上来说的,而且在最深刻的层次上,也是从欲望上来说的。在他们自己欲望的中介下,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与他者相联系了。”巴迪欧的解释,将主奴辩证法的关系更加推进了一步,主人或者主体的欲望在于得到奴隶或他者的承认,而获得承认的条件是成为奴隶和他者的欲望,这样,他们才能具有对欲望的欲望。 在视频游戏或电子游戏中,游戏玩家和游戏角色构成了一种新型的主奴辩证法。我们仍然可以依照科耶夫的逻辑来推进:(1)玩家与角色的关系是玩家通过游戏角色指向设定的游戏目的,角色成为玩家达成通关游戏的中介;(2)游戏角色认同玩家的控制,即玩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对角色的绝对掌控,这是实现游戏通关目的的前提条件;(3)游戏角色能否通过,实际上不仅仅取决于玩家的控制,而是取决于在游戏世界中角色的欲望,如更高的得分奖励,更好的武器装备,更多的魔法和武功秘籍。如果游戏角色得不到经验上的升级,得不到更强大的武器和装备,得不到更好的招式,事实上游戏基本上没有行进下去的可能,这样,玩家和角色的辩证关系就如同主奴辩证关系一般颠倒了。为了达到通关目的,玩家必须对游戏角色进行养成,如在《传奇》《暗黑破坏神》之类的游戏中,玩家必须强迫自己进行枯燥无聊的刷怪升级、刷装备等,并置于游戏的主线,打倒最终的大Boss反而成为游戏中的次要目的。角色的欲望成为玩家的欲望,游戏角色获得了相对于玩家之外独立的生命力,他们这种生命力在于更好地接受玩家的控制,这是一种对欲望的欲望。 游戏角色本身的欲望成为了玩家的欲望,在《无尽之剑》中,太阳剑的获得成为比通关更重要的目的。在一些在线游戏中,为了得到一些特定的装备或秘籍,就必须刷固定时间的活动或副本。如《明日之后》在每天会公布一个固定时间的“感染者入侵”活动,而玩家会牺牲掉正常作息时间,来完成这个活动。在这个辩证关系中,我们看到的是玩家支配游戏角色的反面,为了配合游戏角色的经验增值和收集武器装备的欲望,玩家变成了一个反向的提线木偶,他们必须按照游戏世界中的角色来重新营造自己的生活,对于长期玩某一个游戏的玩家,他们会特定留出某个时间段来完成副本、排位赛或活动。这种状况,很容易联想起当年《开心农场》游戏有玩家定闹钟半夜3点起来偷菜的状况。 玩家和角色的关系被颠倒了,不是游戏角色依照玩家的生活节奏在运行,而是玩家适应着角色在游戏世界中的生命角色。这就是德勒兹式的第三条线,一条反向的提线木偶,木偶支配着傀儡师,而游戏角色支配着玩家,我们仿佛看到了另一个生命的存在,一个仅仅在赛博空间或游戏世界里存在的生命,正在将它的看不见的操纵线附着在电脑屏幕或手机屏幕之后的玩家身上,让玩家变成它们的傀儡。 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全新的概念来界定玩家-角色辩证关系之中的角色的状况。正如在《超级马里奥》中那个不太听从使唤的水管工一样,我们在游戏中感觉到的是一个游戏角色正在抵抗着我——操作游戏的主体的存在,它仿佛具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我们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真实的有机生命,只是因为这些类似《头号玩家》中帕西法尔一样的角色,拥有了类似有机生命的生命一样,我们可以称之为“拟-生命”(quasi-life)。 实际上在电子游戏流行之前,有思想家已经关注了一种类似于“拟-生命”的范畴。如鲍德里亚曾经说过:“在我看来,客体几乎在燃烧,或至少它想拥有自己的生命,它可以抛弃使用的被动性而谋求自主性,或许甚至谋求一种对过度控制它的主体进行复仇的能力。客体一直被视为一个惰性而沉默的世界,按照我们的意志去行事,基于我们创造了它这一事实。但是对我们来说,那个世界想要倾吐其使用性以外的东西。”对于一个抵抗着主体的客体世界或物的世界,鲍德里亚的本意是,希望通过对客体体系(物体系)的探索,来打破主体相对于客体的霸权,但是在这个研究中,他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即具有生命力,并谋求着反噬主体的“拟-生命”。正如鲍德里亚对大岛渚的影片《感官世界》的分析一样:“主要的波折就是从快感到逻辑,男人主导游戏的初始时的逻辑,向挑战和死亡的逻辑的过渡,即女人冲动下的逻辑——女人成了游戏的主人,而在初始时她仅仅是游戏的对象。”那个作为游戏对象的阿部定,在游戏中被激活,具有了生命,这个生命反噬掉了在游戏之初作为主人的石田吉藏。 一个看似没有生命的东西,在游戏的过程中获得了拟-生命的存在。什么是“拟-生命”?虽然在整个思想史上,对生命的认识都与自然的有机体有关,但是,我们也会赋予其他事物带有生命的概念。如在《西部世界》中的智能机器人,完全具有人的外形,如在第一季里温顺如小白兔一般的智能机器人德罗丽斯,能进行一定限度的思考和反应,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机器人往往也会被认为是具有“生命”的。 这样的生命概念,实际上与是否是自然有机体无关,用大卫德·塔里佐(Davide Tarizzo)的话来说,“这代表着一种绝对价值,即生命的价值,意志的价值,在于自律(autonomy)。”塔里佐的界定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将判断是否具有生命的标准,不再依赖于特定的生物组织的结构,而是取决于是否能够自律。自律的意义不仅仅具有自主的意识或道德自律,更重要的是,它也意味着一种物理层次上的生命自动化。法国技术哲学家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用技术物(technical object)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特殊的类似于具有了生命的对象,西蒙东说:“机器能组成一个紧密的装置,通过协调器(coordinator)来彼此进行交流。两台机器直接进行交流(就像一台主振动器和另一台脉冲同步振动器之间的交流一样),人在其中只是一个存在物,他管理着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为的是让机器之间能够更好地交流。”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拟-生命”具有如下特性:(1)拟-生命当然并非真正的生命,在生理上,拟-生命与真正的生命保持着严格的区别,它是一种拟-状态(quasi-state),但同时不以真正生命为蓝本。(2)这就意味着,拟-生命有着自己的规则,用塔里佐的话来说,拟-生命具有属于自己的规则体系和自律性。这样,作为拟-生命的状态,拥有着相对于他者独立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抗着他者的操纵。(3)在定义上,拟-生命还缺少十分重要的一环,即拟-生命不能脱离其特殊的环境而存在,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拟-生命看成独立的个体。它的拟-生命依赖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同时依赖于一种操作。 具体在游戏之中,拟-生命的存在与游戏的环境密切相关。回到梅洛-庞蒂对于身体行为的设定,我们的生存或生命是在行为中让世界向我们敞开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行为中,世界才向我们呈现为一个世界。换言之,在游戏中,玩家只有通过游戏行为才能打开角色在游戏世界中的“拟-生命”。与梅洛-庞蒂唯一不同的是,拟-生命在游戏世界的敞开,最主要的并不依赖于游戏玩家的身体,甚至不完全依赖玩家的手柄、键盘或触屏的操作,而是依赖角色在游戏世界中的身体,甚至是复数的身体来完成的(如一些游戏会选择让玩家操纵多个角色进行游戏)。当角色在游戏世界里探索并打开世界的时候(因为在许多游戏设定中,角色尚未触及的地方都是黑色的未敞开的区域,只有玩家的足迹经历了某个处所时,这个地方的地图或景观才向玩家敞开)。 例如,《刺客信条3》的刺客海尔森进入一家剧院,暗杀一位在剧场三楼宝箱里的目标,直接过去有被发现的危险,这就迫使玩家操纵海尔森在剧场周围发现暗门和攀爬的道路,并穿过后台,从一个密道走向刺杀目标。在行动之前,这条隐秘的道路并不向玩家揭示,只有在玩家一步步的探寻过程中,它才向玩家呈现出一条不可能的道路,角色海尔森也在探索道路和向对象刺下最后一刀时被激活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玩家按下最后的“刺杀键”(默认是F键)时,海尔森代替玩家感受到一个使命的完成。正如里埃勒·莱博维茨(Liel Leibovitz)说道:“当玩家按下了正确的按键,角色执行了正确的行动,让其完全感受到了预期结果,这就是它自己劳动的果实:‘是我’,玩家会嘟哝道,‘我让它发生了’。” 这样,游戏中的拟-生命的展开,与游戏世界中的探索密切相关。游戏的目的不仅仅是实现对游戏角色的拟-生命进行养成,而是要去创造属于这个拟-生命的生态,海德格尔曾说,我们在此世中的存在,就是一种在世界中筑造出的供我们栖居的处所,海德格尔称之为周围世界,这个周围世界不同于一般世界,即那个客观存在的世界。事实上,我们生存和行为向我们敞开的是一个周围世界,“日常此在的最切近的世界就是周围世界……我们通过周围世界内最切近地照面的存在者作存在论的尝试,一步步寻找周围世界的世界性质”。 周围世界的德文词Umwelt,最开始是由生物学家雅克布·冯·尤克斯考尔(Jakob von Uexküll)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一样生物在世界中的行为和感受不同,他们所触及或者所揭示的世界也不同。比如蜱虫只对哺乳动物的丁酸有反映,于是蜱虫的周围世界就是依靠丁酸的气味构造起来的,对于具体的人来说,世界向我们敞开的意义,也正是我们在世界上栖居和行为所筑造出来的意义,世界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周围世界。 同样,游戏中的拟-生命也不是孤立的存在物,而是相对于它的世界筑造了一个可以让角色栖居的周围世界。利安·米切尔(Liam Mitchell)说:“视频游戏所涉及的操作就是为了打开地图,来掌控一个数字世界,这种操作行为表明了一个态度,即它指向了打开一个一般世界的地图,并掌握一般世界(world in general)。”这样,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玩游戏,打倒最终的Boss通关,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游戏世界里培育着数字化的拟-生命,而围绕这个拟-生命,通过我们的行为(如刷怪、分配经验值、增长技能、寻找装备等)来为拟-生命创造一个供它在游戏世界栖居的周围世界。这是一种游戏的生态学,游戏的生态学表明,游戏中的拟-生命需要通过玩家的操纵行为来实现自己的欲望,在各种活动的中介下,让游戏中的世界向游戏角色敞开,一个供角色栖居的世界,也就是拟-生命的游戏生态学。 不过,对于游戏生态学来说,或者如利安·米切尔所警告的那样。游戏的拟-生命或者游戏生态学的最终目的或许不仅仅是在游戏世界中创造一个供他们栖居的周围世界,而是要打开一般世界的地图,去掌控一般世界。正如海德格尔区分了周围世界和一般世界,一般世界实际上已经跨越了纯粹赛博世界和游戏世界的界面,从而指向了屏幕前的玩家,也就是说,拟-生命和游戏生态学不仅将游戏的数字世界整合为一个世界,而且也整合了玩家所在世界。在Netflix的游戏电影《黑镜:潘达斯奈基》中,那个设计电子游戏《潘达斯奈基》的设计师史蒂芬一开始以为自己控制着自己设计的角色,但是他越来越发现自己反而被一种不知名的力量控制了,他甚至不由自主地将咖啡倒在电脑上,他在房间里大喊大叫,究竟是谁在控制他。 又如2016年在苹果和安卓系统中大热的游戏《神奇宝贝Go》(Pokéman Go)需要不断地捕捉被称为“神奇宝贝”的精灵,并对之进行养成,让不少日本和欧美国家的青少年为之如痴如醉,以至于今天玩《神奇宝贝 Go》的玩家被称为“神奇宝贝一代”。由于游戏的巨大影响力,让一些理论家发现:“对神奇宝贝的欲望至少潜在地让我们面对了一个颠倒的状况,即物理对象和生理欲望并不先于技术下的欲望存在。由于看到了这一点,谷歌不可能宣布,给出玩家想要的东西,恰恰相反,游戏揭示存在着一种力量,强迫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不仅改变了我们与神奇宝贝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与食物、饮料和爱侣的关系,甚至改变我们的主体性。” 于是,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被倒置的提线木偶的关系,还包括以游戏角色的拟-生命构成的游戏生态学的关系,即我们依照游戏中的拟-生命重新构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与现实世界分离的游戏世界或虚拟世界,更重要的是,依照着游戏中的拟-生命统一起来的一般世界。由于游戏世界的存在,我们架构世界的经验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一旦在拟-生命架构的周围世界中建立了新的认知框架,这个认知框架不只停留在游戏世界中,会反过来作用我们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如今天的很多游戏玩家更喜欢从经验值和升级的角度来理解世界,这正是游戏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反噬。在不断数字化的今天,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熟悉的一切,已经被游戏世界的框架还原为一系列游戏式的构造,于是,不是我们的游戏越来越像世界,而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像游戏,新的世代将生活在数字游戏架构的生活世界里,这才是属于他们的世界,一个需要在游戏式的征服和挑战下被重新分配的世界。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4期,原标题为《数码身体、拟-生命与游戏生态学——游戏中的玩家-角色辩证法》。)
从身体现象学到数码现象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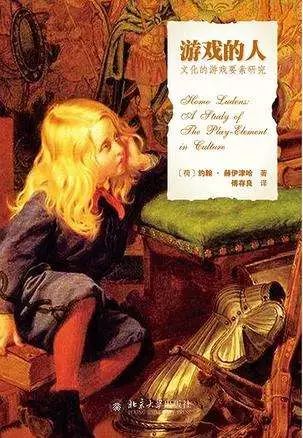




被颠倒的提线木偶



拟-生命与游戏生态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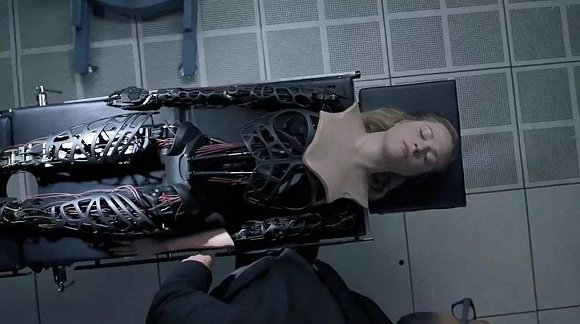


来源:探索与争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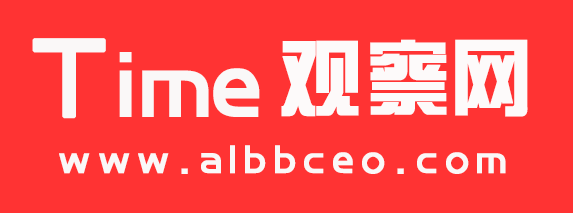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