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Guardian Design
2018年,安娜·伯恩斯凭借讲述北爱尔兰问题的小说《送奶工》斩获布克奖。当被问及写作是否是一种政治行为时,她显然吃了一惊。“这问题是认真的吗?这种问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写的时候并没有往这方面想。”最终她承认,如果政治与权力有关,那么没错,她的作品的确属于政治范畴。奥威尔政治小说奖的评委也注意到了伯恩斯的作品,评委会主席汤姆·萨克利夫(Tom Sutcliffe)称赞《送奶工》“展现了政治立场如何碾碎和扭曲我们人类本性中的忠诚”。
和奥威尔奖的其他入围作品一样,《送奶工》围绕特定主题展开,而未表露明确政治倾向。政治小说的类型总是很丰富,如今阿莉·史密斯、蕾切尔·库什纳、保罗·比蒂和乔纳森·科伊等作家亦可称为政治小说家。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言:“没有一本书是能够真正做到脱离政治倾向的。有人认为艺术应该脱离政治,这种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然而,更难识别的是可能会被称为政治运动小说的作品:查尔斯·狄更斯和埃米尔·左拉等人的经典作品,以及披着小说外衣的宣言、回忆录和报告文学。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希望藉由人物和故事来引导读者关注某些社会弊病,并激励人们作出改良。奥威尔奖评委山姆·雷斯(Sam Leith)曾表示:“现在的小说极力摆脱政治色彩,是不是很糟糕?”
今年5月,萨克利夫宣布奥威尔奖入围名单时坦承“名单偏好那些政治观点隐藏在字里行间,而非直白表露的作品”。科伊的国情小说《英国中产阶级》(Middle England)并未入围长名单,他认为这是评委会对政治倾向明显书籍的“含蓄指责”。“我的感想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响亮、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不管怎么说,就像我在《无赖俱乐部》中塑造的角色道格·安德顿(Doug Anderton)所说,‘含糊其辞是英国人的通病。’我认为这是英国人特有的毛病——在一部政治信息似乎过于明显的小说面前畏畏缩缩。而在法国,参军的作家可以得到额外加分;即使是在苏格兰,詹姆斯·凯尔曼和阿拉斯代尔·格雷等人会被视为民族英雄,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涉及政治内容。但在英国,在文学作品中言及政治似乎会给人留下粗野的形象。”
直白的政治小说总是能引起读者的怀疑。奥威尔曾公开将哈丽叶特·比切·斯托的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归类为“不错的坏书”,这评价可谓粗鲁但一针见血。米兰·昆德拉则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斥为“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惠特克·钱伯斯曾发表一篇令人震惊的评论,称安·兰德的哲学巨著《阿特拉斯耸耸肩》“只有在‘小说’一词降格时才配称为小说……里面的故事只是为了吸引顾客进场,好让兰德小姐推销其政治观点。”
自此,文坛对政治信息的抵制越来越强烈。雷斯认为,主流文化思潮让政治运动小说变得孤立无援。“我们都沉醉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嘉奖一本书不是因为它的主题,而是因为它的文学技巧,”他说道,“你可以基于作品的笔法尽情评判,但你很难评判一个人的思想是否足够有价值。”正是出于对形式和语言的决定性关注,《送奶工》这本不同寻常的书脱颖而出,但所有公开表达改革派政治观点的作者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寒冬。
“学习文学的时候,我们的箴言是: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无关政治的。”乔安娜·卡文纳(Joanna Kavenna)表示。她的最新作品《字母Z》(Zed)讽刺了一家超国家科技巨头的解体。“教材告诉我们,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加到小说中的。但一旦你创造了一个角色或写了一个故事,不论你喜不喜欢,你都会对社会产生看法。”受卡夫卡、果戈里和“不安的传统”的影响,卡文纳更倾向于运用反讽来表达现代生活的奇异感。她认为,带有说教意味的小说更容易被当作政治宣传作品而无法得到公允的评价。“像威廉·莫里斯这样的作家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就是我的政治计划,这些结果正是我想要的。他们对自己和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非常自信。而现在,我们的世界更加变化莫测,观众也更加久经世故。人们对过分直白的陈述非常警惕,以至于我们一直在质疑所有事情的动机。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并非所有读者都排斥政治宣传小说。以《回顾:公元2000-1887年》为例。记者爱德华·贝拉米在书中讲述了一位沉睡了113年,醒来后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平等乌托邦社会的波士顿贵族的故事,借此在美国宣扬社会主义思想。这部长篇小说风行一时,销量奇高,据说比卡尔·马克思的作品更能将美国人纳入社会主义门下。《回顾:公元2000-1887年》对妇女参政主义者、民粹主义者、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威廉·莫里斯、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都产生了影响。艾德礼曾告诉贝拉米之子保罗,二战后的工党政府是“贝拉米理想的产物”。贝拉米并未如其所希望的那样改变世界,但他确实让世界有所不同。
政治运动小说旨在促进立法改良社会,它们确实偶尔能达到目的。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业中移民劳工的困境,其中对肉制品制作过程的描写令人反胃。令辛克莱失望的是,此书并未在改善工人权利上有所建树。不过《屠场》却推动罗斯福政府建立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阿奇博尔德·约瑟夫·克朗宁的畅销书《堡垒》讲述了威尔士一个矿业小镇上一位道德败坏的医生的故事,这本书促使其朋友英国工党领袖安奈林·贝文提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比切·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引发了废奴运动。而罗伯特·特莱塞尔记录英国小镇贫困和剥削的自传体小说《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则如工党议员丹·卡登(Dan Carden)最近所言,“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带来力量。”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兰德激进浮夸的自由至上主义寓言《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拥有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经济学家艾伦·格林斯潘和英国财政大臣萨吉德·贾维德等一众有权有势的门徒。钦努阿·阿契贝撰写的《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是杰里米·科尔宾和巴拉克·奥巴马最爱的作品之一。这部反殖民主义里程碑式作品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记录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分别向全球读者展示了尼日利亚和苏联土地上的巨大不公。以上只是对政治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的冰山一角。但政治运动小说似乎已经过时了,它们急迫的、赤裸裸的声音陷入了沉默。

奥威尔奖现任评委会主任珍·席顿(Jean Seaton)认为,政治运动小说在二战后失势,有其政治因素。许多战前在政治上极具影响力的小说家都信仰社会主义,战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坚持使这些作家的信仰在美学和道德上都令人生疑。
批评家们认为,若哪位小说家希望借作品刺激政治改革,就必须考虑到一个现实问题:当下统治阶层对文学小说的兴趣远不及艾德礼和安奈林·贝文他们那代人。席顿回忆起1960年代前英国工党内阁大臣罗伊·詹金斯掌权的时光:“他会听取别人的想法,并将其转化为实践。现在的高层政治家和行政官员既不会考虑回馈民众,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政治家对政治小说毫无兴趣,作家们也不再自信自己的作品可以影响政治。
唯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英国工党副主席汤姆·沃森,他推崇的作品包括《回顾:公元2000-1887年》和亚瑟·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其中对斯大林时期政治迫害的记录令人大开眼界,“《中午的黑暗》让我真正了解到意识形态是如何被用于镇压民众的。”
不过,政治人物一般不会错误假设政治小说对选民缺乏吸引力,故而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汤姆叔叔的小屋》《回顾:公元2000-1887年》和约翰·斯坦贝克描述尘暴带来的巨大灾难的《愤怒的葡萄》等作品都是轻易登上畅销书宝座的书,它们造成的影响曾迫使政治人物出面回应。但新近出版的小说没有一本能与上述著作媲美,这也反映出小说在更大范围内失去了文化主导的地位。一个世纪以前,小说仍然是作家讲述故事的主要形式,任何想要传播政治信息的作家都希望落笔书写。热衷政治的作家们认为,无论多么虚伪,都有必要在小说中粉饰一下政治倾向。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虚构小说”的兴起使得记者不再需要伪装成小说家。若辛克莱生于21世纪,他很可能决定将《屠场》写成直白的报告文学,《回顾:公元2000-1887年》则可能变成像保罗·梅森(Paul Mason)《后资本主义》(Post Capitalism)那样的宣言。以往作家们不得不将政治观点潜藏在字里行间,而今,约翰·兰彻斯特会根据自己想表达的想法而选择撰写小说或非虚构类作品。

那么坚持写小说的意义何在呢?大卫·西蒙称其作品《火线》是“为电视剧而作的小说”。评论家表示,《火线》对巴尔的摩的影响有如当初狄更斯对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影响。和辛克莱一样,西蒙也是一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记者,他喜欢在《火线》中穿插说教。“我们就是编委会,”谈及编剧会议时他说道,“我们尽可能地利用叙事剧来表达我们的观点。”获得今年奥威尔奖最佳文章的作品题为《<我是布莱克>之后的行政正义》(Administrative Justice in the Wake of I, Daniel Blake),现在还有《火线》这种小说会如肯·洛奇的电视剧《凯西回家》或电影《我是布莱克》那般拥有道德热情和政治影响,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也许将西蒙比作我们这个时代的狄更斯,将洛奇比作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莱塞尔,也未尝不可。“小说在文化领域内没有享受绝对特权的必要,”雷斯说,“就思想的传播方式而言,只要能达到传播之效,那么无论何种媒介都是重要的。”
即便是现在,仍有部分小说家希望影响读者所想。席顿对戴夫·埃格斯适时讽刺互联网的小说《圆环》大加赞赏,称其以惊悚小说的形式具象化了人们对社交媒体的担忧,并在科技和政治领域引发了涟漪。儿童文学作家、编剧弗兰克·科特雷尔·博伊斯表示,青年小说的读者天生好奇心旺盛、充满理想主义,此类小说传递政治观点的功能被远远低估。他将游历甚广的小说家伊丽莎白·莱尔德比作“一位充满热情、富有同情心的外国记者,向读者介绍更广阔的世界”。但他同时担心,苏珊·柯林斯的《饥饿游戏》大获成功后,黑暗的未来已使光明黯然失色。

“我担心大量反乌托邦小说成为潮流,让年轻读者对腐败和谎言见怪不怪,”他说,“我始终认为,小说应该履行的一项重要职责是为读者描绘出一幅美好的图景,但现在似乎并非如此。我觉得,一部小说要想成为真正的政治作品,至少应该展示变革的可能性,指明前进的方向。”
所有的文学潮流都曾经历高峰和低谷,但从各个方面看来,政治运动小说似乎已经陷落。作家、读者、评论家和政治人物对此漠不关心,甚至持怀疑态度。科伊认为,带有政治动机的作者仍将被迫通过更为迂回的途径来获得读者的同情,即使他们更愿意直奔主题。
“我最露骨的两本政治小说《如此瓜分!》(Whata Carve Up!)和《数字十一》(Number 11)在笔法上都相当狡猾,”科伊坦承,“就好像你必须为政治内容道歉,用一些毋庸置疑的‘文学’因素来包装它。”他说,肯·洛奇读过《数字十一》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所有的书评都在赞扬你在这本书中展现的文学造诣,但却甚少言及书中强烈的反紧缩情绪。’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共鸣。我怀疑在这个国家,撰写一部小说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就是被无视个中政治内容后仍能获得嘉许,而不是因为书写政治成名。”
(翻译:刘其瑜)
来源:卫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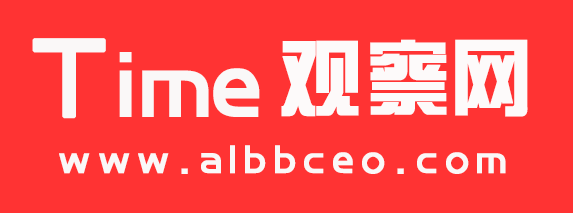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